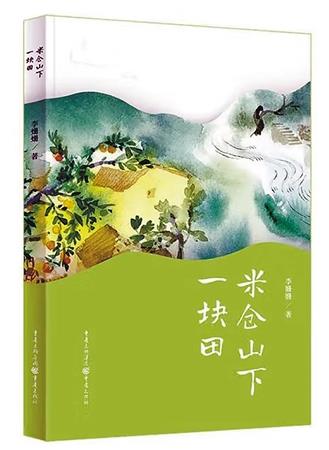
□王玉美
翻开李姗姗所著的《米仓山下一块田》,像是赤脚踩进带着晨露的田埂,土地的呼吸、童年的笑声,混着四季的风声,从字里行间漫溢开来。这不是一本普通的儿童文学,而是一堂大自然的文学课,它以土地为母本、童年为种子,栽种出精神原乡,在书页间搭建起连通乡土与童心、现实与哲思的秘密花园。
书里的土地,是米仓山下真实可触的田,更是乡土记忆的容器。作家以四季为轴,把土地脉动拆成春种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的故事。春天田埂,泥土腥甜藏着种子发芽期待;夏日稻田,蛙鸣稻香缠绕成童年背景音;秋天晒谷场,金黄谷粒折射土地慷慨;冬日冻土,蛰伏着土地默默孕育。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泥土气息,被风雨打磨的农具故事,都在文字里苏醒。关于土地的书写,无刻意雕琢,让土地生态肌理自然生长——土地不再是背景板,而是有呼吸、情绪,能给予也会沉默的生命体。它用四季轮回教孩子懂生长与等待,用作物荣枯述说付出与收获,让乡土从地理概念,变成滋养心灵的精神母体。
儿童视角,是打开土地精神密码的密钥。作家让孩子做土地“第一译者”,用烂漫眼睛看田埂蚂蚁搬家,用童趣思维解庄稼生长。孩子把土地裂缝想成大地皱纹,把稻草人幻想成田园卫士,在他们眼里,土地有灵魂和故事。这种视角,让土地生态内涵可感可触——生态不是晦涩概念,是蚂蚁队列协作、鸟儿啄食平衡、四季轮转秩序。孩子与土地互动,是本真生态教育,没说教,却让“共生”“循环”等生态哲学,悄悄在童年心田播下种子。
李姗姗的文字,是乡土记忆显影的投射。她用童趣意象、诗意语言,把土地故事转化成文字光影。“有些东西虽然暂时不见了,但不是真的不见了,它们变成了记忆,变成了词语”,这样的文字,似把土地魂魄炼成诗句。写土地虫子是“泥土里的音乐家”,写风吹稻田是“稻穗在给风讲古老的故事”。这些灵性文字,让乡土记忆突破时间封印,老农具、旧习俗、土地原始律动,借文字重新显影,在纸上写出生生不息的田。
生态,是书里潜藏的厚重底色。它不站环保立场喊口号,而是把生态融入生命肌理。土地、作物、动物、孩子,在故事里构成循环生态系统:孩子守护鸟巢,鸟儿啄虫,虫儿松土,作物养孩子。这种生态观,是乡土本真的生存智慧,也是对现代性的温柔反思——当城市挤压乡土、人类破坏生态平衡,书里童年与土地的共生,提醒我们回望乡土生态哲学:人从不是土地主宰,是与万物共生的伙伴。
在儿童文学版图,《米仓山下一块田》拓展了乡土叙事边界。它不做简单“乡土怀旧”,用儿童眼睛、生态思维、诗意文字,重构乡土精神维度。以往儿童文学里的乡土多是“童年背景”,这本书让乡土成主角,成为滋养童年、传递生态哲思、连接过去未来的精神原乡。它为儿童文学注入土地厚重、生态深刻、童年本真,让乡土书写从“回忆式乡愁”转向“前瞻性精神滋养”——告诉孩子,乡土藏着生命、自然、与世界相处的永恒答案。
合上书,米仓山下的田仍在眼前生长,四季不停,童年笑声不散,土地故事未完。作者用文字开垦的田,不只是乡土记忆显影池,更是童年精神滋养地、生态哲思播种机。它让我们看见,乡土是儿童文学富矿,只要用童年眼睛挖掘、诗意文字呈现、生态思维解读。这片纸上的田,终会在孩子心田,种下对乡土的爱、对自然的敬畏、对生命的珍视,让乡土精神,在现代浪潮里长成遮风挡雨的森林。





